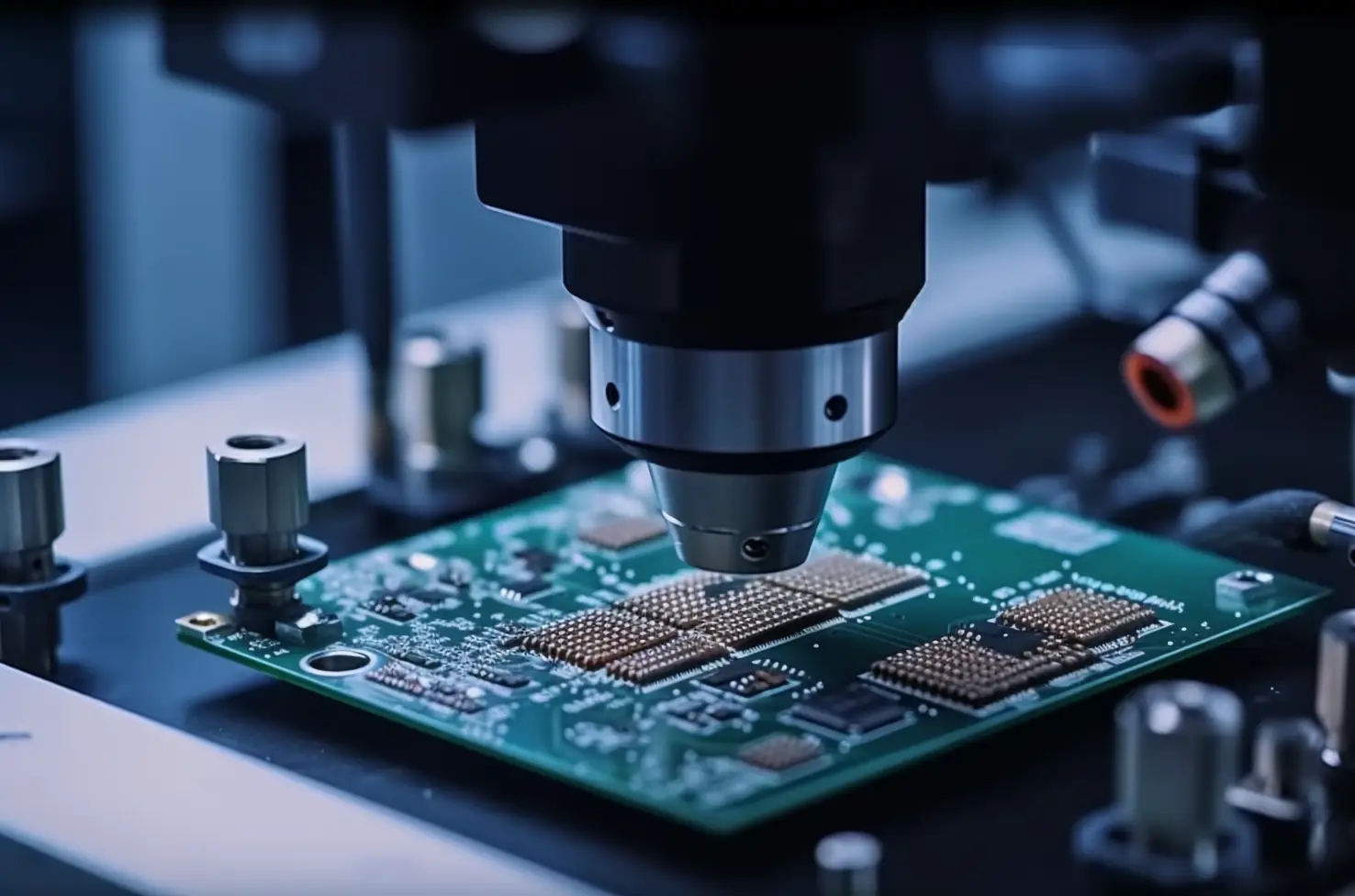近年来,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持续加强并不断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国际恐怖主义仍然此起彼伏、气焰嚣张,其中有着复杂、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第一,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恐怖主义肆虐的罪魁祸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恐怖主义的生存之基。当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对“古兰经”与“先知圣训”等伊斯兰教教义进行曲解和断章取义,歪曲编造民族发展历史,制造“宗教认同”或“民族认同”,主张最终建立所谓的“政教合一、实施沙里亚法的大哈里发国家”,蛊惑追随者实施恐袭活动。其滥杀无辜的行为被国际社会界定为恐怖活动,但在极端分子眼里则是有“教法”依据的“圣战”行为。他们认为,“圣战”是清除“邪恶异教徒”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圣战者”可以通过毁灭他人赢得真主愉悦,“在进入天堂时受到欢迎”。恐怖主义赤裸裸的暴力经过极端主义包装后极具迷惑性和蛊惑性。“伊斯兰国”就援引伊斯兰法和《古兰经》经文编撰一整套论述,以使其杀戮和劫掠行为正当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大约有23万名恐怖分子支持“圣战主义”意识形态。与2001年相比,这一数字增长了400%。它们利用极端思想左右、影响、蛊惑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招募了大量成员、扩充了实力。
另一种是打着白人至上旗号的极右翼意识形态。近年来,极右翼意识形态获得了社会土壤。一方面,西方的政治气候对其有利。在西方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横行的大背景下,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反移民、反难民的排外思潮不断上升,美欧一些国家接连出台排斥、歧视甚至仇视移民的政策,加剧了整个西方政治生态的右转势头,极大刺激了极右恐怖势力的坐大。在美国,奥巴马时期极右极端分子就开始活跃,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发布“禁穆令”、修建美墨边境墙、阻止难民入境等行为更像是“让美国再次白人化”而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表示,特朗普制造了“让暴力的极端分子猖狂”的环境。在欧洲,民族主义主张和极右翼政党已经获得了显著支持。美欧的右翼暴力与传统政治相交织,加深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分野,使极右翼的影响力大增。“从极右翼演变为极右翼恐怖主义”的倾向已经引起关注。另一方面,西方对外政策尤其是反恐中的“双重标准”对其有利“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只注重遏制、打击那些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思想,对宣扬白人至上的极端思想却视而不见且未采取有效措施。间接对极右恐怖势力的蔓延起到了助推作用。近期,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将通过一项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网络审查”的行政命令,以确保社交媒体公司不会对保守派抱有“偏见”,该举措将使科技公司更难打击网络上的极右极端主义。
第二,宗教矛盾与教派冲突是国际恐怖主义尾大不掉的直接原因。宗教矛盾与教派冲突一直是极端势力用以煽风点火、浑水摸鱼的主要抓手。一方面是西方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它是现实,又是历史,持续了数百上千年。二战结束以来,双方之间对立、冲突的真正根源是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冷战时期,美基于国家利益考量数次介入中东战争、插手中东事务、扶持以色列打压“两伊”(伊朗、伊拉克)等行径,使西方与穆斯林渐行渐远。冷战结束后,美西方企图确立世界新秩序、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尤其是美借“反恐战争”在中东强推“植入式民主”,加剧了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作为西方式民主试验田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地不仅未成“民主样板”,反而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然而,美西方并未就此罢手,就连“伊斯兰国”都声称西方正与伊斯兰“开战”。随着2019年新西兰“3·15”恐袭事件和斯里兰卡“4·21”恐袭事件的爆发,原有宗教矛盾显得更加激化且更难调和,并成为西方极右恐怖势力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相互仇视、相互发难并诉诸暴恐行动的工具,以致形成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伊斯兰国”造成可乘之机。“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头目扎卡维在给本·拉丹的效忠信中明确提到,计划通过掀起一场恐怖风暴,杀害更多的什叶派信众,以引发激烈的宗派斗争。其目的就是破坏伊拉克局势,消灭一些“叛教人员”;同时裹挟逊尼派信众,迫使他们拿起武器,为了“解放”而斗争。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为此策动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如2003年8月29日针对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纳杰夫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精神领袖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吉尔·哈基姆等95人死亡;2006年2月22日针对伊拉克什叶派圣地萨马拉城阿斯卡里清真寺的袭击事件,炸毁由7.2万块金板铺就的金色穹顶。此类事件成功挑起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相互敌对与仇视,引发严重的教派冲突。到 2014年,经扎卡维点燃的宗派危机之火已席卷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伊斯兰国”崛起期间,其头目巴格达迪故技重施,利用教派矛盾在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鼓动许多深感被残害、被边缘化、遭什叶派排斥的反叛逊尼派。“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攻城掠地就是从逊尼派聚居地开始的,因为这些地方的穆斯林本来就对什叶派政府不满,认为其故意剥夺他们的权利。
当前,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集中体现为沙特与伊朗的对峙。沙伊矛盾兼具教派积怨、地缘争夺和安全困境等多重内涵,因而逐渐成为地区局势变动的主线。一旦中东教派矛盾被固化,甚至出现两个以教派作为身份认同、相互对立的阵营,其结果很可能是冲突旷日持久,而且愈演愈烈,进而继续成为恐怖组织利用的工具。
第三,地缘政治矛盾是国际恐怖主义威胁难以消除的国际背景。恐怖主义思想传播、恐怖主义肆虐的背后往往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沉疴,诸如政治矛盾尖锐、经济发展落后、社会两极分化、族群对立、政府管控力弱等等。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域外力量干预下,深陷动乱甚至战争的泥潭,更容易成为恐怖主义蔓延的温床。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引发阿富汗战争,促成“基地”组织的兴起;美错误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基地”组织在伊有了可趁之机,叙利亚内战又使“伊斯兰国”迅速崛起。英前首相布莱尔曾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日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负有部分责任。“9·11事件”后,美及其西方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打破了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政治均衡状态。一方面,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威权主义政权濒于瓦解或不复存在,遏制恐怖主义的强大力量消失;另一方面,地区政治秩序的崩塌形成巨大地缘政治真空,为恐怖势力滋生蔓延、坐大提供了机会。
2018年12月,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执行主席斯蒂夫·基勒里解析“2018年全球恐怖指数报告”时指出,“冲突和战争是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在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10个国家中,所有国家都至少卷入了一场暴力冲突,8个国家卷入了一场重大战争。”
当前,中东再现代理人战争,整体局势更加动荡、混乱。由于美对伊朗频繁实行“极限施压”,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美盟友沙特的多处石油设施,还频繁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的机场,加剧了该地区的混乱局势。“伊斯兰国”借机频繁活动、策动恐怖袭击。2019年8月30日,其在也门首都亚丁策动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利比亚内战濒临爆发,卡扎菲倒台以来政局持续动荡,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两派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断。
2018年以来,“伊斯兰国”已在利比亚策动20多起恐袭事件。南亚阿富汗战乱连连,“阿塔”与政府军长年对峙,“伊斯兰国”趁势迅速渗入。2019年8月17日,“伊斯兰国”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婚礼现场策动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63人死亡、182人受伤,因此,阿富汗独立100周年纪念庆典不得不延期。印度莫迪政府宣布取消宪法第370条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权,导致印巴局势更不太平,此前“伊斯兰国”已宣布在此建“省”。有斯里兰卡官方消息称,“4·21”爆炸案主谋、后经确认身亡的扎哈兰·哈希姆曾在印度待了近三个月,并打了十几个电话,可能在克什米尔接受过训练。这些动荡与战乱地区政权争夺与宗派主义、好战倾向、高失业率、社会歧视等始终错综交织,成为“伊斯兰国”“基地”及其他本土恐怖组织的“避风港”。
第四,大国力量与美俄博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推手。首当其冲的是,国际反恐的大国牵引力下降。随着“伊斯兰国”在伊、叙被挫败,加之“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在美欧本土策动的外源性暴恐大案减少,作为国际反恐主要推动力量的美欧对国际反恐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明显减少。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是发生重大变化,重点由打击恐怖主义转向大国竞争,现已将中俄视为头号威胁、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美最新《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重新崛起是美国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美在国际反恐中的投入比重大幅度下降,对外计划从阿富汗、叙利亚撤军,并放弃支持伊拉克、阿富汗的“国家重建”;对内强调保护本土、预防袭击和一旦遭袭击减轻损失,已将其本土作为其反恐的“主战场”。
与此同时,美俄博弈的加剧导致国际反恐形势的恶化。借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斗争,中东出现了美俄并存替代美国一家独大的战略格局,地区主要矛盾由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转向地缘政治博弈。俄巩固在叙利亚的影响,与伊朗、土耳其不断走近,进一步嵌入中东、牵制美国。美缺乏反制措施,因此不断加大对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孤立、封锁和制裁。
美俄借打击恐怖主义进行的大国博弈与地缘战略之争尤其美“遏伊扶以”的政策,削弱了国际反恐力量。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将“反恐”当成了打压伊朗的借口。美新版《国家反恐战略》屡屡强调伊朗是“全球头号支恐国家”,因此反恐就必须遏制伊朗。为此,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伊全方位施压,如退出伊核协议,取消中、印、土等八国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权,企图将伊朗石油的出口压缩到零;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宣布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进行制裁;连续两次向中东派兵,频繁派无人机侵犯伊朗领空,并实施网络攻击等系列措施,致使美伊对峙不断升温,其实质是“项庄舞剑”,意在对付俄罗斯。相应地,美国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推出所谓“世纪协议”。其明显偏袒以色列的立场和行径使巴以局势更加复杂,也加剧了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给“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留下了可钻的空隙。
内容来自《现代国际关系》
 优投APP下载
优投APP下载 优投服务号关注
优投服务号关注